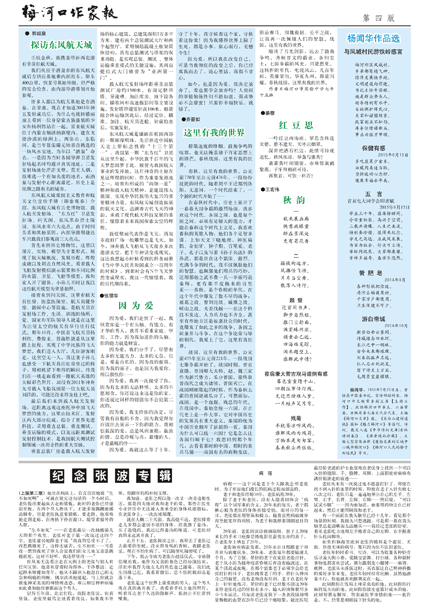
怀念爸爸四题
(上接第三版)他坐在病床上,自言自语地说“生不如死啊”。可就在说完这句话的一个小时后,老张提出要起床去走廊锻炼。此时的老张已经虚弱至极,在两个男人搀扶下,才能步履蹒跚地挪动脚步。但是老张执意要锻炼,要走路。他艰难地走到走廊,在搀扶下停在窗口,凝望着窗外的人群。
“生不如死”——在老张最后一次抽搐前几天的那个夜里,老张对老于第一次说过这四个字。老张虚弱地跟老于说“我真的忍受不了了,我想跳楼死了,这样太痛苦,生不如死……可是我一想到我死了别人会说我们的女儿他父亲是跳楼而死,这样不好听,我还得坚持……”
你从来无法看出走在大街上的老张与别人有任何区别,他喜欢穿着时尚得体,干净整洁,走起路来矫健如青年,他从不跟别人抱怨自己的无奈和病痛的纠缠,偶尔淡淡地提起,马上你就会被他神采奕奕的神情所迷惑,难以相信种种病痛如此叠加地折磨眼前这个男人。
记得五年前,北京住院,我跟老张说,你真坚强。老张坚毅笃定地看着我说,如果我不坚强,你跟你妈妈如何支撑。
我知道,老张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奇迹般生还,都是因为他对我和老于的爱。那些在医生专业评估中无法被人类承受的身体机能指标,在老张身上,一次次被颠覆。
就在大概二十天前,我高烧不退,老张撑着走几步都会虚弱不堪的身体,给我熬了姜汤,买了退烧药。我还记得姜汤的味道,可老张却真的永远离开我了。
正月十五,老张圆坟之日,我带去了老张过去最爱的生蚝,没来得及喝的香槟。我跟老张说,现在不怕生病了,可以随便吃随便喝了。
下午,我去寺庙为老张办超拔仪式,寺庙僧侣规劝我,他作为父亲的角色已经扮演结束,浮世中我作为他女儿的角色也已谢幕,我们此生因缘已近。我看着僧侣,忍不住的眼泪还是落下来。
老张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这个男人现在真的离开我了。我看着手机上他的照片,听着耳边老于久违的微鼾声,眼泪止不住留到嘴角。
病程
病程——这个词是老于今天跟我念叨老张时,为了形容他们漫长的抗病过程而创造的。
老于和老张结婚30年,老张病程20年。
除了老于和老张,没有人能真切体会“病程”这个词厚重的含义,20年来的每天,老于都揪心般为老张的身体担惊受怕。而对应的每一日,老张都在用坚强和毅力,拖着虽然病痛缠身却坚挺宽厚的肩膀,为老于和我撑着朗朗旭日的天。
20年前,老张因误诊被摘除胆,肚子上20厘米长的手术刀疤像恐怖电影里蚕食生命的虫子,在老张身上栖息了20年。
老张被疾病蚕食着,20年来日日都跟老于肩并肩与病魔抗争。20年来,老张每年都要输液几个月,为了方便,晕针的老于在家给老张打针。老于从小因为接种疫苗昏厥后再没有输液过,在某个清晨或夜晚,在那个需要老于必须学会给老张打针的日子,老张拽着老于的手,将针头伸向自己的血管。没有老师没有培训,老于在老张身上一针针地练习,晕针的老于已经数不清这20年来给老张扎过的针眼有多少,输入的液体要用多少卡车运送,只知道老张皮肤下一条条浅绿却明显黝粗的血管在20年后已经干瘪暗紫,就连医院最经验老道的护士也很难在老张身上找到一个可以入针的缝隙,手、胳膊、双脚,上面都密密麻麻布满针眼游走的痕迹……
老张从未有一次说过他不愿意打针了,即使在找不到入针的血管的时候,即使在老于入针失败七八次之后,老张只是一遍遍地伸出自己的左手、左臂、右手、右臂、左脚、右脚……然后说,“可以试试小腿”……因为他知道,他要用药物让自己好起来,然后才能照顾我和老于。
有一个画面在我头脑里已经十几年,看见那个场景的时刻,我扭头只想逃跑,可是那一幕在我头脑里总是清晰而无法磨灭——我经过老张的卧室,看见老张吃力地用左手搬着自己的左脚,右手握着针头扎向脚背。
如果你脑海里此刻老张的模样是个虚弱、无助、彷徨无神的病号,那只因为你不认识老张。
老张年轻时看书、写诗、可以为收集各种轻音乐寻遍大街小巷,爱跳交谊舞、打台球、各种新鲜事物他都喜欢尝试,偶尔跟朋友小赌博……麻将、棋牌,老张从未落伍过时,买衣服让自己精神抖擞的爱好多年未变。老张年轻时经常应酬,虽然他酒量不行,但他就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此刻跟你在饭局上神采奕奕的他,此刻跟你打麻将侃大山的他,此刻跟你谈生意算计成本的他,此刻帮朋友解围、帮亲戚张罗事情的他——也许是,不,经常是刚刚拔下针头的他。